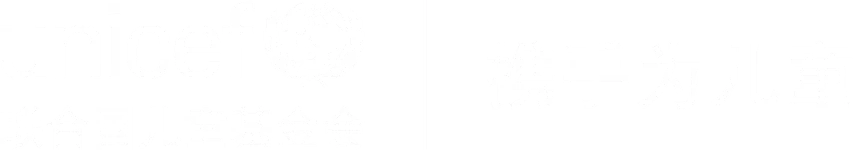我期待一个更有包容性的数字环境
我们不应被数字技术定义,而是应该用数字技术去赋予彼此无限的可能性。

- 可选语言:
- 中文
- English
作为第一代数字原住民和视力障碍者,我的生活和所有人一样,甚至更深刻地依赖于数字技术构建的世界。
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我们接收到的内容越发原子化和碎片化,信息过载和偏见成为当今我们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残障者也和所有人一样,也在思考和尝试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无障碍的、跨残障的数字协作环境,为有抱负的残障者提供创新的平台。
残障的身份本身带给我们更丰富的思考角度,有时候对于某些信息,换一种感官体验会更直接或深入。
我因为疫情导致的国际运输不畅无法回家,在最想家的时候听朋友在一款纯听觉的虚拟航空模拟游戏中带我飞越洲际航线回到熟悉的家乡。这款游戏完全由视障航空爱好者开发和维护,当我朋友降落之前开始播放来自小时候的旋律时,我体会到残障者可以创造的情绪和社会价值不止步于被社会偏见所认为的那样,总是需要帮助和怜悯。相反,残障者能够也应当参与到更多创新性生产的环节中去,提供真正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前提是,我们有一个对残障者足够友好的数字生产和教育环境。
现实是,我们面向生产与协作的数字技术环境依然没有足够的包容性。当我因为平台无障碍的问题不能去查找信息真实来源,只能被二手情绪宣泄裹挟的时候;当我发现在做一个需要跨国线上讨论的协作项目,却因为平台无障碍问题无法协调统一工具的时候;当我尝试找到一个不仅视力障碍友好且价格足够低廉,还对非技术背景人群有足够低门槛的协作工具而无果的时候;网络似乎被撕裂成为了一个个孤岛和“信息茧房”,方便大家走出舒适区去聆听新观点的可能性似乎被堵死了。
想打破这样的局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反思。我们需要去讨论我们要用技术和网络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一定希望有目的和有方向的积极使用数字技术,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随时抽离。因为我们知道:数字技术背后的是人,更有效和灵活安全的联结我们的经历和喜怒哀乐才是数字技术诞生的初衷。因此我们需要去了解数字技术背后的机制,进而更好地掌控数字技术。而这一切,离不开数字技术在更专业领域的开放和包容性。
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我们有公平使用数字技术的权利基础之上。我们需要一个无障碍的专业数字环境,让包含残障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更深入的“跨圈”交流。
曾经被用来发布求助信息的协作文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真正有需要的和希望提供支持的人可以得到真实和有温度的互动,也让人们看到了互联网能产生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巨大价值。然而当时其中一些平台的无障碍问题却排除了残障者参与的可能性,让这一部分人群的声音被淹没在杂乱的信息当中。我参与的“少数派”线上跨残障社群因为网上的求助渠道信息无法支持屏幕阅读器(读屏软件)的访问,专门对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做了图片转文字和人工校对工作,然后再重新发布。发布的时候我们依然无法做到完全的无障碍,许多平台的后端文稿管理界面对屏幕阅读器用户依然不友好。这些问题本不应该存在,残障者是大众的一份子,他们却不能实现应有的使用数字技术协作的权利。在数字环境没有充分实现无障碍的情况下,我们更难以谈论残障文化带来的思维模式创新和对社会的推动与促进。
如果没有关注语言障碍者以及听力障碍者的沟通需求,我们的合成语音也许不会如此自然高效,智能音箱也许不会如此便利且有亲和力;如果没有联觉者和对世界有特别感知的人群,我们就不可能有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艺术生命力,许多微小的洞察也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视障者的参与,有声书和有声剧行业也许不会如此丰富多彩,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也许不会发现“听书”的魅力。
人类的多样性推动我们走到今天,也让我们更能适应不同的环境,带给我们生活下去的希望和脱离“数字糖精”与“信息茧房”的勇气。多样性对人类的促进作用只会变的更加明显和意义深远。它比数字技术本身更古老更永恒,是伴随我们人类的不变的话题。
因此我们希望学习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我们希望做一群变局者,我们想说:比无障碍的娱乐和社交媒体环境更重要的,是给残障者和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个无障碍的专业协作环境。
这个环境需要人人可以参与,不论他们有何种残障;它需要具有包容性,让所有人能够主动思考,发出自己可以掌控的、更有完整性的声音。我们不应被数字技术定义,而是应该用数字技术去赋予彼此无限的可能性。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改变和尝试新领域的权利。